阿特拉斯
不说话,然后呢?
郑玄将重拾手语视为寻找自我的“钥匙”,但即使在聋人社区内,对于这种方法也存在分歧。
聋哑人群是多元化的,包括手语使用者(以手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口语使用者(以口语为第一语言的人),以及像郑轩这样的人同时掌握两种语言的她,总是进退两难。手语使用者和 口语 使用者之间的分歧是聋人社区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会说话的聋哑人不认同手语,认为只要有一点学习口语的可能,一定要牢牢把握,让自己回归“正常”,学不会除非他们能学会手语。但对于手语使用者来说,他们认为作为聋哑人,手语是群体的标志,“是身份的象征”。
郑玄想要找到那个平衡点,却发现很难走下去。她理解双方的问题,“为什么手语的人对使用口语的人不满意?作为语言少数群体,他们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甚至手语翻译有时也无法准确传达他们的意思。”意图……表达的需求被压抑了很久,他总会爆发。对于口语的用户来说,说话意味着能够接近主流的聆听世界,这会带来很多便利。而这个机会是手语使用者,即使它是非常困难的有能力并且经常无法获得。”
就算选择不说话,这之后的路要怎么修,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近几年,市面上流传最广的手语参考书是中国聋人协会2003年编着的《中国手语(上下修订版)》,俗称“黄书”。这两本书总共只有5600多字。郑玄说,这本书实用性不高,聋人社区不认可。“字多,人设痕迹明显,离聋子的语言太远了。其实就像小时候学英语,我们在学中文英语。”
相比之下,聋人通用手语的语法顺序不同,词汇更丰富,其形成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1887年中国第一所聋校的建立。此外,还有手语方言。不同地方的语言。武汉手语、重庆手语、上海手语都有词汇差异。
聋人的手语大多是从生活和人际交往中逐渐习得的。郑玄也来到重庆,对聋人进行了实地考察。他才知道当地的“朝天门”和“小场口”是如何用手语表达的,他还是第一次发现老人和年轻人的手语有很大的影响。词汇差异。“有很多正宗的手语演奏方法语言学英语,需要从社会上一点一点地收集,然后进一步研究,但还没有被系统地发现。”
2018年5月,《全国通用手语通用词汇》发布。在这本书的编纂过程中,聋人参与的比较多,但郑玄表示,很多常用词仍然没有收录,而且书中的一些文体在聋人中间还是有争议的。
还有其他先决条件需要解决。在重庆聋校,雷鸣仍然是唯一一个失聪的老师。学校还想招聘更多的聋教师,但人手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因为备考意味着要有教师资格证,而资格证包括普通话考试,这对聋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政策有所松动,普通话考试改为手语考试,但实际操作仍难推进。雷鸣在重庆聋校工作了十年。还是外人。
2020年,郑轩有了新的开始。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聋教育系的一位退休教师向郑轩发出了邀请。调至北京后,郑轩主要研究方向为手语与听力障碍教育。这几年郑璇忙得不可开交,去北京让她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科研。她还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做出更多改变的机会,为那些“选择不说话”的人和他们的家人找到一条更宽、更顺畅的道路。(文/本报记者梁婷)
3
3
+1
阿特拉斯

郑轩在讲解手语

重庆聋校教学楼上写着“无声也很精彩”

郑轩(左)与聋校老师手语交流
郑玄是励志人生的模板。
她两岁时就失去了听力。经过长期的口语康复训练,她考上了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后赴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博士。在中国的聋人语言学和大学教学。
在聋人的世界里,试图与口语交流是大多数人心目中最理想的状态。相比之下,手语被污名化了。看到郑轩,不少家长信心满满,“我家孩子说不定会说话,也能上大学。”
但郑璇并不想成为父母追捧的“康复明星”。
在漫长的口语康复训练中,她经历了太多的孤独和艰辛。在聋人与听人之间的世界(注:聋人指的是健全人),郑璇遭遇了身份危机,双方一度将她视为“与众不同”。
成年后,一直小心翼翼地使用口语,“躲”在正常人极度压抑的世界里的郑璇做出了新的选择,她开始“放手”口语,学会了手语,真正康复了。自己。
“手语是一种可能。我们的生活可以有其他选择,我们有选择不说话的权利,任何选择都没有错。”
尝试接近正常人
每年都有很多家长来郑轩语言学英语,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复制“努力接近正常人”的故事。
郑璇曾将她的耳聋归咎于她两岁时吸毒。后来,她得知自己有导致耳聋的基因,患上了“大前庭导水管综合症”。多年来,她的听力持续下降,目前已降至 100 和 120 分贝。不过比起先天聋哑的孩子,她还是幸运的。在她耳聋的时候,积累了一点口语基础,属于语后聋,是更好的康复训练的前提。
家人尽了最大的努力让郑玄回到“正常的世界”。为了方便她读儿歌,她买了一台双卡收音机,这在1980年代是奢侈品;祖母早早退休照顾她,而在海军服役的父亲则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回到了家乡;年老时语言学英语,全家去香港买了几百元的盒式助听器。他们以郑萱为中心,从“a、o、e”开始,将知识一点一点地“吼”进她的世界。
坐在小板凳上,无数次地重复着发音,这是郑轩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父母在她耳边夸张地张嘴大叫,她想起了空气喷在她脸上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偶尔调皮一下,大声说话,然后大声地逗大人,她得把那个字念成百上千遍。

“那是一段非常令人不安的记忆。感觉就像在训练一只鹦鹉。” 她已经学了半年多的Z、C、S的发音了。妈妈原本害羞腼腆,但在抚养她的过程中,她逐渐变成了一个声音特别响亮的人。
从小学开始,郑璇就一直在普通学校读书,努力让自己“更像一个正常人”。她尽量依靠助听器,听不清楚就模仿。她睁大眼睛观察周围的人。小学老师开玩笑说,郑璇一边听课,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恨不得被吃掉。
一年级的时候,郑玄经常不知道老师让他做什么。数学课上,看到同桌拿出一捆棍子,她也默默地从书包里拿出来,配合着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猜她要数数。“当时我还太小,助听器不起作用,听不清楚,也不知道如何表达。”
音乐老师教大家唱歌,但她根本听不懂,只好学着动嘴。回到家后,她模仿歌词的发音问父亲:“抱住我是什么鬼?” 她这才知道,完整的歌词应该是国歌中的“Breaking the Fire of the Enemy”。
很多时候,她都忍着,假装明白。她努力消化所有降临在她身上的困难,让自己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优秀和完美。在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中,她获得了全区第一名。
但“接近正常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教室的黑板上经常写着“聋”两个字;门框上放着一把扫帚,等她推门;助听器也被抢走…… 高中时,同桌的三个同桌要求她在一个学期内与她分开。她性子沉闷,不爱说话,但喜欢用文字说话。她的大多数同学都认为通过写作交流太麻烦了。
1
1
+1
阿特拉斯
从隐瞒到接受
现在的郑璇淡定了许多,遇到人也毫不避讳自己耳聋的身份。第一次见面时,她总是提醒对方站在自己的左侧,因为只有左耳还有一点高频听力。如果是在餐厅等公共场所,嘈杂的环境影响助听器的效果,她会把脸转向一边,让对方重复她说的话。
这是一个从隐瞒到接受的过程。
在上大学之前,郑璇从来没有和她的聋哑同伴接触过。她一步步将自己隐藏在“正常人”的世界里,时刻带着随身听,随时录音、修正、重复,希望自己的声音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她的声音和语调越来越自然,但直到她考上只招收25名学生的武汉大学国家人文实验班,她还在努力融入,仍然自卑。
室友是学校电视台的主持人,也是辩论队的辩手。郑玄很欣赏会说话、形象好、有男朋友的人。室友把别的学校的男生介绍给她,见面时她都不敢说话。为了避免尴尬,室友一直主动,男孩爱上了她的室友。“当时我心情很不好,自卑到极点,连水都泼到头上博士 在聋人语言学中:选择不说话并快乐,好几次想过辍学。”
郑璇试图自救,在“聋人在线”论坛上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聋人朋友。他们在武汉大学门前的草坪上相遇,她互相学习手语,第一次不用尝试说话。他们用手机打字、添加表情和动作,仍然可以拼凑出彼此的意思。她忘记了自己学到了什么,前世难得一小时的幸福,她看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此之前,郑玄常常因为没有听清楚别人的话而感到难过和羞愧。“见到他后,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听不见不是我的错。我们是聋子,我们就是这样。”
聋友介绍郑轩加入湖北省残疾人艺术团。她结识了更多的聋人,了解了聋人世界的“规矩”。“这种感觉仍然伴随着她。
她曾因在网上发表评论而招致批评。郑玄当时写道:“只要我们聋人够努力,够优秀,也能找到健全人做终生伴侣。” 她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据说聋人比听人好。当别人指出这一点时,她意识到在倾听的环境中长大很难改变自己的想法。
在残疾人文工团排练的时候,她曾经很纳闷,为什么一开始有些聋子对她很热情,然后突然就冷了。后来才知道,有一次,当聋人指挥老师用手语跟大家讲一些事情时,她转过头来和碰巧进门的听力老师打招呼,移开视线,不理会手语,“他们以为我不想和聋人说话。沟通。”
回到“听人说”的世界,郑玄也有些不自在。导师让她在本科班上谈谈她的论文。她不想上台,说话也变得困难。即使别人说她发音很好,她也很注意每个单词,如果她发音不完美,那就很痛苦。
两个圈子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度体现在身上。郑轩病倒了,请了几个月假才回学校。
一次偶然与美国小辈的交流,帮助郑璇走出困境。我弟弟会说中文,他的手语非常好。《身份危机》,郑轩第一次听到了“身份”这个概念,“他告诉我,很多聋人长大后都会经历这样一段时期,我当时好像开悟了。原来如此这是一种文化现象,我并不孤单。”
在此之前,郑璇一直觉得自己是隐藏在听众中的异类,厌倦了长期的压抑。她问自己:“我能完全放弃听者的身份,接受自己是个聋子吗?” 她给她的导师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我不能用手语说话和表达吗?教练回复:当然,你可以选择你觉得舒服的生活方式。现在回想起来,她说那是她心中的一道坎。只有彻底“放下”口语,手语才能进步,才能真正体会到寂静世界的感觉。
如果你选择不说话,你会很开心
博士毕业后赴重庆师范大学任教。除了教课,她还担任了近80名聋哑学生的班主任。当郑璇终于完成了自我认知,她遇到了越来越多前来咨询的聋哑父母。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重复郑玄曾经走过的路——口齿伶俐,会说话。
听力障碍已成为我国第二大出生缺陷,0-6岁儿童超过80万,每年新增聋儿3万。郑轩说,目前聋儿家长往往只能得到医生的建议:“送康复中心。” “去做人工耳蜗。” 一个聋哑人的成长故事。他们不知道手语其实是一种语言,学习手语也可以实现交流。
口语一旦康复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语言学英语,就会导致聋儿第一语言的建立迟缓,认知、智力和社交能力都会落后于常人。郑璇不想成为父母追捧的“康复明星”。这条路有太多坎坷,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她自己的口语康复有很多前提条件——听力残留,早期使用助听器,父母为了她几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目前的康复技术虽然有所改进,但也不是100%可复制的。”
“猜猜这是什么意思?” 郑璇左手比划着数字六,食指和中指并拢,在六人中间轻轻抚摸。她解释说,在手语中,刘的手势代表“人”,而伸出的剑意为“刀”。刀切在人体上,就是手术的意思。在重庆人喧闹的餐厅里,郑轩不断变换着姿势,表达着从地名到情绪的各种表情,“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大家都懂手语,就不用拉一起。大声喊出来,对吧?
这是郑轩的美好愿景,但在现实中,手语仍被一些人等同于“耻辱”。尽管手语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已有六十年的历史。
在郑轩接触的一些家长中,很多都羞于让孩子手语,却让孩子年复一年地完成枯燥的口语训练,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正常人”,有的“上岸”,有些明显看不到效果,也不愿意坚持。
在重庆聋校工作了20多年的周迅红记得,曾有家长直接去学校,拒绝教孩子手语。
这所学校唯一的聋哑老师雷明小时候就被手语说服了,“手语很美,有灵魂。我的家人让我说口语,但我总是很沮丧在说话的过程中,我只是想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 学完手语后,雷鸣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不用强迫自己说话,她感到很幸福。
郑轩说,手语本质上是一种视觉语言,更加直观、生动、简洁。她希望更多人会手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拒绝口语。“能学当然很好口语,但如果学起来很难,或者没有条件学习,也不要勉强自己。就算口语恢复得很好,同时学习手语,更多掌握一门语言,多一种交流方式又有什么关系呢?”
手语是一种可能,聋孩子的父母应该知道,生活中还有其他选择,而不仅仅是口语一种方式。郑玄的观点是,当聋童没有选择能力的时候,让他接触尽可能多的语言,给父母看每一条路。“在双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往往会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优势。成长让他们自己做决定,任何一种选择都没有错。”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阿卡索学习网 - 英语学习培训机构网站! > 博士 在聋人语言学中:选择不说话并快乐
 今年北京国际高中学费多少,贵不贵
今年北京国际高中学费多少,贵不贵 实验中学牵手名校 借势成为“名校”
实验中学牵手名校 借势成为“名校” 、英语、英语三家对比,这样选才好
、英语、英语三家对比,这样选才好 从日语到升学,行知长沙校全部为你准备好
从日语到升学,行知长沙校全部为你准备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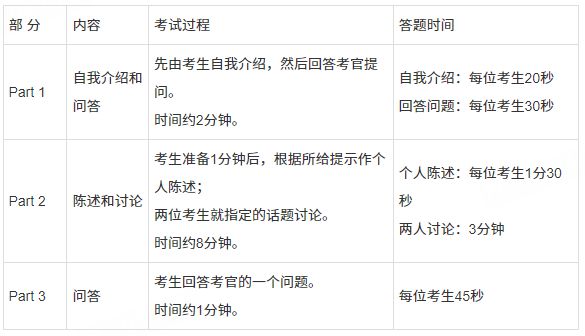













热门信息
阅读 (2353)
1 张雪峰直言:这三个大学专业“失宠”,就业率低,报考需谨慎阅读 (2068)
2 适合高中英语学习的25部英文电影,太好看了,你看过几部?阅读 (2009)
3 old man不是“老人”的意思,下次别翻译错了阅读 (1777)
4 全国小学生英语能力测试(NEPTP)申请指南【文末有福利】阅读 (1151)
5 英语一对一用什么教材?哪个是最好的?